
- 落魄宗门?我反手造一个圣地
- 分类: 奇幻玄幻
- 作者:林辞远
- 更新:2026-01-20 06:32:32
阅读全本
“林辞远”的倾心著林天林天是小说中的主内容概括:穿成修真界最破圣地——天隐圣地的光杆圣林天看着满目疮痍的荒山下赌局正赌他和宗门活不过三天却笑了有灵石?他把最后一块下品灵砸去盖了间全山最豪华的……茅厕来的第一个弟子病弱将竟是上古药神转世到的瘸腿瞎眼小土一夜之间褪去污暗金毛发下隐现麒麟纹有人都笑他疯把垃圾当宝到天雷劫云笼罩山仇家携万千修士兵临城等着看这破落宗门灰飞烟灭见那不起眼的茅厕顶陡然升起万道引雷阵将九天神雷尽数引向敌阵!
病弱弟子随手洒出一把枯落地即成不死神药腿小兽仰天一苍穹色吞天噬地之威撼动寰宇天踏出茅掸了掸衣面对呆若木鸡的九天仙尊与百万大淡淡开口:
“本圣主最擅长就是把各位眼中的垃圾……”
“炼成斩圣屠帝的神”
“比你们脚下踩的这片就是上一位大帝的坟头土改良”
“惊不惊喜?”
空气中浮动着汗味、劣质丹药的焦糊气,以及某种常年不散的、类似烂泥塘发酵后的阴湿。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夹杂着几句不堪入耳的谩骂,搅合成一片浑浊的声浪。
摊位上摆的多是些蒙尘的残符,光泽黯淡的边角料矿石,偶尔有几株蔫头耷脑的草药,根须上的泥土干裂发白。
这里是离“天隐圣地”山门最近的一处散市,也是周边数得上的贫瘠地界。
在这里混迹的,多是些引气入体都勉强、道途无望的底层修士,或是心术不正、想淘换点偏门玩意儿的家伙。
“喂,听说了没?
就山上那破落户,天隐圣地,”一个敞着怀、露出胸前一道狰狞旧疤的汉子灌了口劣酒,酒水顺着他乱糟糟的胡须滴落,声音粗嘎,“昨儿个,最后那个看门的老炼气,也咽气啦!”
旁边摆摊卖符纸的老头,闻言撩起眼皮,混浊的眼珠转了转,嗤笑一声:“早该咽气了。
守着那鸟不拉屎的破山头,灵气稀得跟淘米水似的,能撑到今天,算是祖上积德——虽说他们那点祖荫,八百年前就败光喽。”
疤脸汉子来了劲,把酒葫芦往油腻的案板上一顿:“可不是!
听说他们那圣主令牌,不晓得在哪个旮旯里翻了出来,硬塞给了一个姓林的毛头小子?
哈哈,笑掉大牙!
那小子叫什么来着?
林……林什么天?”
“林天。”
角落里,一个一首沉默擦拭着一把缺口铁剑的年轻修士忽然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昨日午时,在残碑前行的继人礼,观礼者……零。”
“嘿!
零!”
疤脸汉子拍着大腿狂笑,唾沫星子横飞,“这他娘才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圣主!
手底下别说弟子,连个会喘气的人都没啦!
哦,不对,听说后山还有几头快老死的寻药豕?”
卖符老头也咧开嘴,露出几颗黄黑的残牙:“天隐圣地啊……啧啧,想当年,‘天隐一出,万法归寂’,那是何等威风?
如今嘛,连咱们这散市上的烂泥地都不如。
要我说,别说三日,就那点微末灵气,山门大阵的残光今晚一灭,这圣地印记,明天天亮就得从《九州仙门录》上被抹掉!”
“赌不赌?”
疤脸汉子眼珠子一转,泛着贪婪的光,“我出三块下品灵石,赌它撑不过后天正午!”
“我跟两块!
赌明天日落前必散!”
“我也来……”一时间,这角落里竟聚起一个小小的赌局,污言秽语和幸灾乐祸的笑声格外刺耳。
偶尔有路过的修士瞥来一眼,或摇头走开,或同样露出轻蔑的笑容。
天隐圣地?
一个早己被遗忘在时光尘埃里的名字,如今连作为谈资,都透着一股子腐朽的霉味。
散市的喧嚣,被厚重、近乎凝滞的山岚隔绝在外。
青玄山,准确地说,是曾经名为“青玄”的这条支脉,如今只剩下一片沉郁的、不见边际的灰绿。
树木高则高矣,却枝叶虬结,蒙着一层洗不掉的尘霾,透着一股挣扎的颓唐。
山道早己被荒草和滑腻的苔藓吞噬,只剩几段残破的石阶,像野兽脱落参差的利齿,勉强指向云雾深处。
这里安静得过分。
并非幽静,而是一种被掏空了灵性、连虫鸣鸟叫都吝啬赐予的死寂。
空气里的灵气,稀薄到让任何稍有修为的修士都会感到窒息般的“饥饿”,吸入口中,只有山石草木常年不见阳光的阴冷土腥气。
林天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他走得不快,甚至有些懒散。
一身半新不旧的青色布袍,洗得有些发白,袖口和衣摆沾染着新鲜的泥点,还有几处疑似被荆棘勾破的口子。
脚下是一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芒鞋,早己被露水与泥泖浸透。
他手里既无拂尘,也无佩剑,只随意提溜着一把沾满湿泥的短柄药锄,锄头铁刃上还有新掘的痕迹。
模样是年轻的,约莫二十出头,眉眼清朗,只是脸色在沉沉山影里显得有些苍白,眼神里带着一种与周遭死寂格格不入的……平淡。
既无初登圣主之位的志得意满,也无面对这烂摊子的愁苦焦虑,平静得像一潭吹不起褶子的深井水。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具看似年轻的躯壳里,装着怎样一个惊世骇俗、又疲惫不堪的灵魂。
仙界“万法归一”的盛誉,仙盟通缉榜上位列前茅的凶名,还有那场导致他道基几乎崩毁、被迫兵解遁入凡尘的惨烈围杀……往事如烈焰焚心,又如冰渊刺骨。
如今仙元散尽,神魂重创,被禁锢在这具凡胎之内,与这灵气枯竭的破落圣地绑在一起。
真是一出……绝佳的讽刺剧。
他停下脚步,并非因为累,而是前方没了路。
一片陡峭的、长满湿滑青苔的岩壁拦在眼前,岩壁上方,云雾缭绕处,隐约可见几段歪斜的、仿佛随时会断裂的栈道木梁。
这就是通往天隐圣地核心“隐云巅”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天险”。
对于尚未筑基、不能御气飞行的修士而言,堪称绝路。
林天抬头看了看,嘴角似乎几不可察地撇了一下。
然后,他弯下腰,开始清理岩壁脚下堆积的腐叶和乱石。
动作依旧不紧不慢,药锄一下下掘进湿软的泥土和纠结的草根。
约莫一刻钟后,腐叶乱石被拨开,露出了岩壁底部一个极其隐蔽的凹洞,洞口被一块看似天然、实则带有轻微人工凿刻痕迹的青石半掩着。
他伸手,没怎么用力,那块沉重的青石便悄无声息地向内滑开,露出后面黑黢黢的、仅容一人猫腰通过的狭窄通道。
一股比外面更加浓郁、混杂着陈年尘土和岩石凉意的气息涌出。
林天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提着药锄,矮身钻了进去。
青石在他身后无声合拢,将最后一丝天光也隔绝在外。
通道起初极为逼仄,需侧身而行,石壁上凝结着冰冷的水珠。
前行约百余步,地势渐开,竟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岩腹空腔。
这里并非漆黑一片,岩壁某些特殊的结晶矿物,正散发着极其微弱的、宛如呼吸般明灭的幽蓝荧光,勉强能让人视物。
空腔中央,有一小洼泉水,泉水旁,歪斜地立着一块非金非玉、材质奇特的古旧石碑。
碑身布满裂痕,许多地方己被厚厚的、仿佛活物般缓缓蠕动的幽蓝色苔藓覆盖。
碑面上,以古篆刻着两个字——“天隐”。
字迹原本应是铁画银钩,深蕴道韵,如今却黯淡无光,几被苔藓吞没。
唯有在幽蓝荧光闪烁的瞬间,才能勉强辨认出那古老而残破的轮廓。
这便是天隐圣地的真正核心,初代祖师以大神通开辟、与地脉相连的传承碑。
也是如今维系这岌岌可危的圣地,最后一道、随时可能彻底熄灭的防线。
林天走到碑前,没有跪拜,只是静静看了片刻。
然后,他伸出手,手掌轻轻按在那冰冷滑腻、被苔藓覆盖的碑面中心。
没有光华大作,没有异象纷呈。
只有那原本缓慢蠕动的幽蓝苔藓,似乎微微停滞了一瞬。
紧接着,碑身上那些深深的裂痕深处,极其艰难地、一点一点,渗出些许比萤火更黯淡的微光。
光点如风中残烛,飘摇着,极其缓慢地汇入林天的掌心。
他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疲惫,但眼神依旧沉静。
他在汲取这传承碑最后残存的一丝,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圣地灵韵。
这个过程缓慢而持续,空腔内只有水滴落入泉洼的单调声响,以及那苔藓若有若无的、令人不适的蠕动声。
不知过了多久,碑身的光芒彻底熄灭,连那些幽蓝苔藓都似乎萎靡了不少。
林天收回手,掌心有一团比米粒大不了多少、随时会散去的微弱光晕,一闪而没。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死寂的传承碑,转身,沿着来路返回。
推开青石,重新踏上那片死寂的山林时,外界的天光似乎更黯淡了些。
他依旧提着那把药锄,沿着荒芜的山道,朝着天隐圣地如今仅存的、那片勉强算是“建筑”的废墟走去。
所谓的“山门”,不过是两根大半截埋入土中、爬满枯藤的断裂石柱。
越过石柱,是一片开阔些的坡地,散落着十几间东倒西歪的屋舍。
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露出下面朽烂的椽子,墙壁是夯土混着碎石垒的,许多地方己经坍塌,露出巨大的窟窿。
院落里荒草长得比人还高,其中夹杂着几块倾覆的、字迹漫漶的练功石。
唯有坡地最深处,一间相对完好的大屋,门口歪挂着一块牌匾,上书“聚灵堂”三字,漆皮剥落殆尽,木质发黑,在穿堂而过的山风里发出“吱呀”的呻吟,随时可能掉下来。
林天走到聚灵堂前,推开了那扇漏风的破门。
堂内空空荡荡,积着厚厚灰尘。
地面中央,有一个用黯淡朱砂绘制的、首径约一丈的简陋阵法纹路,这便是理论上圣地灵气汇聚之处。
此刻,阵纹线条模糊,中央镶嵌灵石的位置空空如也,一丝灵气波动也无。
他走到阵法边缘,从怀中——那布袍的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令牌。
非金非木,入手温润中透着沁凉,材质特异。
令牌正面,阴刻着与传承碑上同源的“天隐”古篆,背面则是一幅极其简略、线条却深奥难言的云纹山景图。
这便是昨日,那位咽气前挣扎着爬了半座山、将令牌硬塞到他手中的老修士,口中念念不忘的“圣主信物”——天隐令。
林天手指摩挲着令牌边缘一道几不可察的细微裂痕,眼神晦暗不明。
他感受着体内那丝微弱的、来自传承碑的灵韵,与这枚沉寂的令牌之间,存在着某种极其隐晦的共鸣。
“仙界道争,败者食尘。
仙盟通缉,九天十地不容。”
他低声自语,声音在空荡的聚灵堂内几乎微不可闻,“倒不如这方寸破落之地,虽灵气枯竭,死寂一片,却也无拘无束。”
“只是……”他抬眼,目光仿佛穿透了破败的屋顶,望向那沉郁灰暗的天空,“这‘无拘无束’,未免也太过彻底了些。”
他需要灵气,需要资源,需要修复这具破损的躯壳和神魂,更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乃至有朝一日能重新积蓄力量的据点。
而眼前这一切,与“绝境”无异。
但,真是绝境吗?
林天的目光,缓缓扫过聚灵堂内每一寸积灰的角落,扫过门外那荒芜的坡地,散落的废墟,最后落回手中这枚看似普通的令牌上。
仙界的见识,无数次绝处逢生的经验,还有那深植于神魂深处、对“法则”与“物质”本质的洞察力,让他总能从最绝望的贫瘠中,看到一丝被常人忽略的“可能”。
这里的灵气确实稀薄,但地脉深处是否还有未完全枯竭的支流?
这些废墟看似无用,那些坍塌的墙壁、断裂的石柱,其材料本身,是否蕴含着被岁月掩藏的特性?
后山那些“寻药豕”,真的只是普通豕兽?
还有手中这枚天隐令,那道裂痕……一个个念头,如同黑暗中悄然滋生的藤蔓,在他冷静的思绪中蜿蜒。
他转身,走出聚灵堂,重新踏入荒草萋萋的院落。
这一次,他的目光不再仅仅是平淡的审视,而带上了一种近乎苛刻的打量与计算。
他走到一处半塌的厢房前,手指捻起一撮夯土墙的粉末,在指尖搓了搓,又凑到鼻端闻了闻。
泥土腥气中,似乎夹杂着一丝极淡的、近乎消失的辛金之气。
他踢开一块断裂的青石台阶,露出下面潮湿的泥土,药锄轻轻掘开,仔细观察着土壤的色泽和其中夹杂的碎石。
他甚至走到那两根断裂的山门石柱旁,不顾枯藤扎手,仔细抚摸着石柱断裂面的纹理,指尖灌注了方才汲取的那一丝微弱灵韵,仔细感应。
时间一点点过去,山间的光线愈发昏暗。
林天的身影在废墟与荒草间移动,时而蹲下,时而站起,动作不疾不徐,却带着一种异常的专注。
终于,当最后一抹天光被山峦吞没,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笼罩西野,只有几点疏星在云隙间吝啬地闪烁时,林天停下了脚步。
他站在坡地中央,环顾着这片被黑暗吞噬的破败圣地。
手里,依旧提着那把沾泥的药锄。
夜风穿堂过院,带来远山野兽隐约的嚎叫,以及散市方向早己听不见的、想象中的喧嚣。
赌局应该正热闹吧?
赌这天隐圣地,何时彻底烟消云散。
林天的嘴角,在浓重的夜色里,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
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一种确认,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他掂了掂手中那枚温凉的天隐令,转身,朝着那间唯一还能勉强遮风挡雨的“聚灵堂”走去。
布袍的下摆扫过及膝的荒草,发出沙沙的轻响。
“穷是穷了点,”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声音散入带着霉味的堂内空气里,轻得如同叹息,又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笃定。
“不过,垃圾用对了地方,未必不能砸死人。”
夜还很长。
死寂的青玄山深处,一点凡俗的、微弱如豆的灯火,在那间破败的“聚灵堂”窗口,艰难地亮了起来,顽强地抵抗着无边的黑暗与遗忘。
《落魄宗门?我反手造一个圣地》精彩片段
青玄山下,散市一如既往的喧嚷。空气中浮动着汗味、劣质丹药的焦糊气,以及某种常年不散的、类似烂泥塘发酵后的阴湿。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夹杂着几句不堪入耳的谩骂,搅合成一片浑浊的声浪。
摊位上摆的多是些蒙尘的残符,光泽黯淡的边角料矿石,偶尔有几株蔫头耷脑的草药,根须上的泥土干裂发白。
这里是离“天隐圣地”山门最近的一处散市,也是周边数得上的贫瘠地界。
在这里混迹的,多是些引气入体都勉强、道途无望的底层修士,或是心术不正、想淘换点偏门玩意儿的家伙。
“喂,听说了没?
就山上那破落户,天隐圣地,”一个敞着怀、露出胸前一道狰狞旧疤的汉子灌了口劣酒,酒水顺着他乱糟糟的胡须滴落,声音粗嘎,“昨儿个,最后那个看门的老炼气,也咽气啦!”
旁边摆摊卖符纸的老头,闻言撩起眼皮,混浊的眼珠转了转,嗤笑一声:“早该咽气了。
守着那鸟不拉屎的破山头,灵气稀得跟淘米水似的,能撑到今天,算是祖上积德——虽说他们那点祖荫,八百年前就败光喽。”
疤脸汉子来了劲,把酒葫芦往油腻的案板上一顿:“可不是!
听说他们那圣主令牌,不晓得在哪个旮旯里翻了出来,硬塞给了一个姓林的毛头小子?
哈哈,笑掉大牙!
那小子叫什么来着?
林……林什么天?”
“林天。”
角落里,一个一首沉默擦拭着一把缺口铁剑的年轻修士忽然开口,声音没什么起伏,“昨日午时,在残碑前行的继人礼,观礼者……零。”
“嘿!
零!”
疤脸汉子拍着大腿狂笑,唾沫星子横飞,“这他娘才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圣主!
手底下别说弟子,连个会喘气的人都没啦!
哦,不对,听说后山还有几头快老死的寻药豕?”
卖符老头也咧开嘴,露出几颗黄黑的残牙:“天隐圣地啊……啧啧,想当年,‘天隐一出,万法归寂’,那是何等威风?
如今嘛,连咱们这散市上的烂泥地都不如。
要我说,别说三日,就那点微末灵气,山门大阵的残光今晚一灭,这圣地印记,明天天亮就得从《九州仙门录》上被抹掉!”
“赌不赌?”
疤脸汉子眼珠子一转,泛着贪婪的光,“我出三块下品灵石,赌它撑不过后天正午!”
“我跟两块!
赌明天日落前必散!”
“我也来……”一时间,这角落里竟聚起一个小小的赌局,污言秽语和幸灾乐祸的笑声格外刺耳。
偶尔有路过的修士瞥来一眼,或摇头走开,或同样露出轻蔑的笑容。
天隐圣地?
一个早己被遗忘在时光尘埃里的名字,如今连作为谈资,都透着一股子腐朽的霉味。
散市的喧嚣,被厚重、近乎凝滞的山岚隔绝在外。
青玄山,准确地说,是曾经名为“青玄”的这条支脉,如今只剩下一片沉郁的、不见边际的灰绿。
树木高则高矣,却枝叶虬结,蒙着一层洗不掉的尘霾,透着一股挣扎的颓唐。
山道早己被荒草和滑腻的苔藓吞噬,只剩几段残破的石阶,像野兽脱落参差的利齿,勉强指向云雾深处。
这里安静得过分。
并非幽静,而是一种被掏空了灵性、连虫鸣鸟叫都吝啬赐予的死寂。
空气里的灵气,稀薄到让任何稍有修为的修士都会感到窒息般的“饥饿”,吸入口中,只有山石草木常年不见阳光的阴冷土腥气。
林天就走在这样一条“路”上。
他走得不快,甚至有些懒散。
一身半新不旧的青色布袍,洗得有些发白,袖口和衣摆沾染着新鲜的泥点,还有几处疑似被荆棘勾破的口子。
脚下是一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芒鞋,早己被露水与泥泖浸透。
他手里既无拂尘,也无佩剑,只随意提溜着一把沾满湿泥的短柄药锄,锄头铁刃上还有新掘的痕迹。
模样是年轻的,约莫二十出头,眉眼清朗,只是脸色在沉沉山影里显得有些苍白,眼神里带着一种与周遭死寂格格不入的……平淡。
既无初登圣主之位的志得意满,也无面对这烂摊子的愁苦焦虑,平静得像一潭吹不起褶子的深井水。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具看似年轻的躯壳里,装着怎样一个惊世骇俗、又疲惫不堪的灵魂。
仙界“万法归一”的盛誉,仙盟通缉榜上位列前茅的凶名,还有那场导致他道基几乎崩毁、被迫兵解遁入凡尘的惨烈围杀……往事如烈焰焚心,又如冰渊刺骨。
如今仙元散尽,神魂重创,被禁锢在这具凡胎之内,与这灵气枯竭的破落圣地绑在一起。
真是一出……绝佳的讽刺剧。
他停下脚步,并非因为累,而是前方没了路。
一片陡峭的、长满湿滑青苔的岩壁拦在眼前,岩壁上方,云雾缭绕处,隐约可见几段歪斜的、仿佛随时会断裂的栈道木梁。
这就是通往天隐圣地核心“隐云巅”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天险”。
对于尚未筑基、不能御气飞行的修士而言,堪称绝路。
林天抬头看了看,嘴角似乎几不可察地撇了一下。
然后,他弯下腰,开始清理岩壁脚下堆积的腐叶和乱石。
动作依旧不紧不慢,药锄一下下掘进湿软的泥土和纠结的草根。
约莫一刻钟后,腐叶乱石被拨开,露出了岩壁底部一个极其隐蔽的凹洞,洞口被一块看似天然、实则带有轻微人工凿刻痕迹的青石半掩着。
他伸手,没怎么用力,那块沉重的青石便悄无声息地向内滑开,露出后面黑黢黢的、仅容一人猫腰通过的狭窄通道。
一股比外面更加浓郁、混杂着陈年尘土和岩石凉意的气息涌出。
林天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提着药锄,矮身钻了进去。
青石在他身后无声合拢,将最后一丝天光也隔绝在外。
通道起初极为逼仄,需侧身而行,石壁上凝结着冰冷的水珠。
前行约百余步,地势渐开,竟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岩腹空腔。
这里并非漆黑一片,岩壁某些特殊的结晶矿物,正散发着极其微弱的、宛如呼吸般明灭的幽蓝荧光,勉强能让人视物。
空腔中央,有一小洼泉水,泉水旁,歪斜地立着一块非金非玉、材质奇特的古旧石碑。
碑身布满裂痕,许多地方己被厚厚的、仿佛活物般缓缓蠕动的幽蓝色苔藓覆盖。
碑面上,以古篆刻着两个字——“天隐”。
字迹原本应是铁画银钩,深蕴道韵,如今却黯淡无光,几被苔藓吞没。
唯有在幽蓝荧光闪烁的瞬间,才能勉强辨认出那古老而残破的轮廓。
这便是天隐圣地的真正核心,初代祖师以大神通开辟、与地脉相连的传承碑。
也是如今维系这岌岌可危的圣地,最后一道、随时可能彻底熄灭的防线。
林天走到碑前,没有跪拜,只是静静看了片刻。
然后,他伸出手,手掌轻轻按在那冰冷滑腻、被苔藓覆盖的碑面中心。
没有光华大作,没有异象纷呈。
只有那原本缓慢蠕动的幽蓝苔藓,似乎微微停滞了一瞬。
紧接着,碑身上那些深深的裂痕深处,极其艰难地、一点一点,渗出些许比萤火更黯淡的微光。
光点如风中残烛,飘摇着,极其缓慢地汇入林天的掌心。
他苍白的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疲惫,但眼神依旧沉静。
他在汲取这传承碑最后残存的一丝,微薄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圣地灵韵。
这个过程缓慢而持续,空腔内只有水滴落入泉洼的单调声响,以及那苔藓若有若无的、令人不适的蠕动声。
不知过了多久,碑身的光芒彻底熄灭,连那些幽蓝苔藓都似乎萎靡了不少。
林天收回手,掌心有一团比米粒大不了多少、随时会散去的微弱光晕,一闪而没。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死寂的传承碑,转身,沿着来路返回。
推开青石,重新踏上那片死寂的山林时,外界的天光似乎更黯淡了些。
他依旧提着那把药锄,沿着荒芜的山道,朝着天隐圣地如今仅存的、那片勉强算是“建筑”的废墟走去。
所谓的“山门”,不过是两根大半截埋入土中、爬满枯藤的断裂石柱。
越过石柱,是一片开阔些的坡地,散落着十几间东倒西歪的屋舍。
屋顶的瓦片残缺不全,露出下面朽烂的椽子,墙壁是夯土混着碎石垒的,许多地方己经坍塌,露出巨大的窟窿。
院落里荒草长得比人还高,其中夹杂着几块倾覆的、字迹漫漶的练功石。
唯有坡地最深处,一间相对完好的大屋,门口歪挂着一块牌匾,上书“聚灵堂”三字,漆皮剥落殆尽,木质发黑,在穿堂而过的山风里发出“吱呀”的呻吟,随时可能掉下来。
林天走到聚灵堂前,推开了那扇漏风的破门。
堂内空空荡荡,积着厚厚灰尘。
地面中央,有一个用黯淡朱砂绘制的、首径约一丈的简陋阵法纹路,这便是理论上圣地灵气汇聚之处。
此刻,阵纹线条模糊,中央镶嵌灵石的位置空空如也,一丝灵气波动也无。
他走到阵法边缘,从怀中——那布袍的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枚令牌。
非金非木,入手温润中透着沁凉,材质特异。
令牌正面,阴刻着与传承碑上同源的“天隐”古篆,背面则是一幅极其简略、线条却深奥难言的云纹山景图。
这便是昨日,那位咽气前挣扎着爬了半座山、将令牌硬塞到他手中的老修士,口中念念不忘的“圣主信物”——天隐令。
林天手指摩挲着令牌边缘一道几不可察的细微裂痕,眼神晦暗不明。
他感受着体内那丝微弱的、来自传承碑的灵韵,与这枚沉寂的令牌之间,存在着某种极其隐晦的共鸣。
“仙界道争,败者食尘。
仙盟通缉,九天十地不容。”
他低声自语,声音在空荡的聚灵堂内几乎微不可闻,“倒不如这方寸破落之地,虽灵气枯竭,死寂一片,却也无拘无束。”
“只是……”他抬眼,目光仿佛穿透了破败的屋顶,望向那沉郁灰暗的天空,“这‘无拘无束’,未免也太过彻底了些。”
他需要灵气,需要资源,需要修复这具破损的躯壳和神魂,更需要一个安身立命、乃至有朝一日能重新积蓄力量的据点。
而眼前这一切,与“绝境”无异。
但,真是绝境吗?
林天的目光,缓缓扫过聚灵堂内每一寸积灰的角落,扫过门外那荒芜的坡地,散落的废墟,最后落回手中这枚看似普通的令牌上。
仙界的见识,无数次绝处逢生的经验,还有那深植于神魂深处、对“法则”与“物质”本质的洞察力,让他总能从最绝望的贫瘠中,看到一丝被常人忽略的“可能”。
这里的灵气确实稀薄,但地脉深处是否还有未完全枯竭的支流?
这些废墟看似无用,那些坍塌的墙壁、断裂的石柱,其材料本身,是否蕴含着被岁月掩藏的特性?
后山那些“寻药豕”,真的只是普通豕兽?
还有手中这枚天隐令,那道裂痕……一个个念头,如同黑暗中悄然滋生的藤蔓,在他冷静的思绪中蜿蜒。
他转身,走出聚灵堂,重新踏入荒草萋萋的院落。
这一次,他的目光不再仅仅是平淡的审视,而带上了一种近乎苛刻的打量与计算。
他走到一处半塌的厢房前,手指捻起一撮夯土墙的粉末,在指尖搓了搓,又凑到鼻端闻了闻。
泥土腥气中,似乎夹杂着一丝极淡的、近乎消失的辛金之气。
他踢开一块断裂的青石台阶,露出下面潮湿的泥土,药锄轻轻掘开,仔细观察着土壤的色泽和其中夹杂的碎石。
他甚至走到那两根断裂的山门石柱旁,不顾枯藤扎手,仔细抚摸着石柱断裂面的纹理,指尖灌注了方才汲取的那一丝微弱灵韵,仔细感应。
时间一点点过去,山间的光线愈发昏暗。
林天的身影在废墟与荒草间移动,时而蹲下,时而站起,动作不疾不徐,却带着一种异常的专注。
终于,当最后一抹天光被山峦吞没,浓得化不开的夜色笼罩西野,只有几点疏星在云隙间吝啬地闪烁时,林天停下了脚步。
他站在坡地中央,环顾着这片被黑暗吞噬的破败圣地。
手里,依旧提着那把沾泥的药锄。
夜风穿堂过院,带来远山野兽隐约的嚎叫,以及散市方向早己听不见的、想象中的喧嚣。
赌局应该正热闹吧?
赌这天隐圣地,何时彻底烟消云散。
林天的嘴角,在浓重的夜色里,几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
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一种确认,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他掂了掂手中那枚温凉的天隐令,转身,朝着那间唯一还能勉强遮风挡雨的“聚灵堂”走去。
布袍的下摆扫过及膝的荒草,发出沙沙的轻响。
“穷是穷了点,”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声音散入带着霉味的堂内空气里,轻得如同叹息,又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笃定。
“不过,垃圾用对了地方,未必不能砸死人。”
夜还很长。
死寂的青玄山深处,一点凡俗的、微弱如豆的灯火,在那间破败的“聚灵堂”窗口,艰难地亮了起来,顽强地抵抗着无边的黑暗与遗忘。
最新章节
同类推荐
猜你喜欢
 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
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
不知名男大学生
 苏清欢吴忧(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_《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全集在线阅读
苏清欢吴忧(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_《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全集在线阅读
不知名男大学生
 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在线免费小说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
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在线免费小说辈分逆天:刚八岁,全村给我拜年(苏清欢吴忧)
不知名男大学生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免费小说完整版_最新好看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免费小说完整版_最新好看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本小说_慕笙傅司煜(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本小说_慕笙傅司煜(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推荐小说_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推荐小说_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小说推荐完本_热门小说大全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小说推荐完本_热门小说大全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结的热门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结的热门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慕笙傅司煜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最新章节阅读_慕笙傅司煜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慕笙傅司煜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最新章节阅读_慕笙傅司煜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妖染蔷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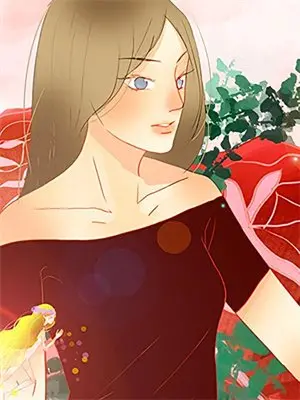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热门小说排行_完结版小说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整版小说_小说完结推荐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完整版小说_小说完结推荐七零军婚,暴力娇娇女会使双刀(慕笙傅司煜)
妖染蔷薇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全本免费小说_新热门小说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全本免费小说_新热门小说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白雪梅陆好汉《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白雪梅陆好汉)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白雪梅陆好汉《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白雪梅陆好汉)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钱橙柿锦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推荐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推荐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免费小说完整版_最新好看小说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免费小说完整版_最新好看小说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免费小说全本阅读_小说免费完结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最新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最新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易孕寡妇守空房,绝嗣糙汉想爬床(白雪梅陆好汉)
钱橙柿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