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基因序列与白月光
- 分类: 霸道总裁
- 作者:汐颜玉溪
- 更新:2026-01-20 02:09:13
阅读全本
霸道总裁《基因序列与白月光讲述主角沈瑶傅时宴的甜蜜故作者“汐颜玉溪”倾心编著主要讲述的是:沈听澜死过一才知道自己是豪门调包计里的真千更是神秘组织“鸢尾项目”编号09-07的实验她的人从出生到死竟是一场被精心设计、观测记录的冰冷实验生归记忆碎如残她藏起锋扮作怯却在暗中淬炼医术与古原以为这是一场针对仇人的复却一步步踏入更深的迷雾:诡异的玉佩空间、接连的匿名警告、南城药渣里的违禁物、边境矿区的亡命追逃……
直到那个同样重生的男人傅时宴出撕开真相:她的“特殊”,早已被觊觎;她的“命运”,从未属于自己日怯懦的真千如今手握足以颠覆一切的核心证在追捕与围困中挣扎求前有庞然大物般的组织“影渊”,后有野心勃勃的豪门秦而她唯一的盟是那个曾为她殉情、如今亦深陷局中的傅时宴是一场始于复仇、终于反抗的征她要挣脱的不仅是仇人的算更是被书写好的、作为“完美实验体”的宿命这一我不做任何人的白月只做斩断所有提线的执刀」
我睁眼的时候,最先感觉到的不是疼,是冷。
雨砸在车顶上,砰砰砰的,跟敲丧钟似的。
然后那疼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胸腔撑满。
“听澜,忍忍……快到了。”
顾言之的声音从右边飘过来,还是那么温和,温和得让人想吐。
我侧过头看他——路灯的光扫过他侧脸,下颌线干净利落,鼻梁挺得可以滑滑梯。
真行,到现在还能演得这么全套。
我指甲掐进手心。
疼,但疼得好,疼得让我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了。
三个月后,也是这条青松路,也是这么个下雨的晚上。
区别是那时候我真信了他的鬼话,真以为他急着送我去医院。
结果呢?
救护车来了,他俯身在我耳朵边说:“瑶瑶需要傅家的股份,所以,你得死。”
说得跟讨论晚饭吃什么似的。
“咳……”喉咙一腥,我偏头吐出口血沫子,溅在浅色的裙子上,像开了朵脏兮兮的花。
“听澜!”
他猛地转头,眉头拧得能夹死蚊子,演技堪称教科书级别,“你别吓我!
都怪我,我不该这么晚还叫你出来……”我闭上眼。
二十五年的记忆跟打翻了的拼图似的,满地碎片。
我记得手术室顶灯刺眼的白,记得沈瑶隔着玻璃对我笑,记得养母躲闪的眼神。
但有些地方是糊的,像蒙了层脏玻璃——我怎么丢的?
傅家到底什么样?
还有……那个总在我快死的时候,在记忆边儿上晃的黑影子,是谁?
“吱——!”
刹车声尖得能划破耳膜。
我整个人往前冲,安全带勒进肩膀,疼得我倒抽冷气。
抬头,车前灯明晃晃地照着路牌——青松路交叉口。
对,就是这儿。
上辈子,一辆货车就是从右边撞过来的,驾驶座首当其冲。
时间,分秒不差。
“言之,”我开口,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我手机……好像掉座位底下了,能帮我找找吗?”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会儿还有心思找手机:“现在?
等到了医院……里面有我妈的照片。”
我垂下眼皮,盯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手指,“就一张……我想看看。”
空气静了两秒。
我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里有多少不耐烦,我门儿清。
但他还是解了安全带,侧过身,弯腰往座位底下摸。
就是现在。
“轰——!!!”
世界在旋转。
不,是车在旋转。
玻璃炸开的声音像一袋子水晶全砸地上了,慢动作似的,一片一片飞过来,映着车灯的光,亮得刺眼。
有温的东西从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右眼。
汽油味冲进鼻子,呛得人反胃。
顾言之在惨叫,声音变了调。
又来了。
黑暗从西面八方涌过来,像潮水。
但这次,胸口忽然烫了一下。
是那块玉。
我低头——血糊住了衣服,但那块从小戴到大的玉佩,隔着布料,正一明一灭地发着热,像颗微弱但倔强的心跳。
“沈听澜!
醒醒!”
这声音尖得跟指甲刮黑板似的。
我猛地睁眼,先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天花板,然后才是沈瑶那张脸——粉底打得够厚,睫毛刷得能扇风,正拧着眉毛看我,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烦。
“你可算醒了。”
她抱起胳膊,身上那件小香风外套价格够我过去一年的饭钱,“发个烧而己,装什么昏迷。
赶紧起来,爸让我接你回沈家。”
回沈家。
我撑着坐起来,手底下的床单又冷又糙。
环顾西周,三人间病房,隔壁床的老太太在咳嗽,空气里一股消毒水混着白菜炖粉条的味道。
窗外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响。
时间对了。
三个月前,我为了给顾言之送他“忘”在公司的破文件,淋雨烧到西十度,自己爬来的医院。
沈家晾了我两天,现在派沈瑶来,施舍似的接我回去。
上辈子,我居然为此哭了一鼻子,以为他们终于想起我了。
哈。
“知道了。”
我掀开被子,光脚踩在地上。
瓷砖冰凉,寒气顺着脚心往上爬。
墙上有面小镜子,我瞥了一眼——里面的人脸色白得跟鬼一样,就左眼角那颗泪痣黑得显眼。
奇怪的是眼睛,明明还是那双桃花眼,里头的东西却好像……不一样了。
沈瑶被我干脆利落的回答噎住,撇了撇嘴:“衣服在柜子里,换好赶紧出来。
麻烦。”
门被她摔上,震得墙灰簌簌往下掉。
我走到窗边,推开玻璃。
风呼地灌进来,带着秋天干爽的、有一点落叶腐烂的气味。
我抬起手,仔细看——二十二岁的手,瘦,指节分明,血管在苍白的皮肤下透出淡淡的青。
还没那些后来磨出来的茧子,还没沾过血,也没救过人。
但这双手记得。
记得银针扎进穴位的微妙触感,记得键盘在指尖下噼里啪啦的脆响,记得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也记得……拳头砸在肉体上沉闷的反弹。
“都还在。”
我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只是记忆像摔碎了的镜子,东一块西一块。
我知道我是谁——傅听澜,傅家被人调了包的真货。
但细节是糊的:怎么被调的?
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傅家到底是龙潭还是虎穴?
还有这玉佩。
我从领口里扯出它。
青色的玉,小拇指指甲盖大,雕着简单的云纹,扔地摊上估计没人多看两眼。
但刚才,它确实烫了我一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摸着它,玉是温的,像活的。
没人回答我。
它静静躺着,像个沉默的秘密。
沈家的车是辆黑奔驰,新得反光。
沈瑶一上车就戴上耳机刷视频,咯咯咯地笑,声音假得不行。
司机是个中年大叔,从后视镜里瞟我,那眼神,跟看一件没摆对地方的行李没两样。
我靠在后座,脸贴着冰凉的车窗。
江城。
这座我活了二十年,死了一次都没能爬出去的城市。
熟悉的街景一帧帧往后跑,像部褪色的烂电影——我在这条街上给顾言之买过咖啡,在那个橱窗前羡慕过一条我永远买不起的裙子,在另一个角落里,哭着接过沈瑶“施舍”的旧衣服。
真他妈够了。
车开进栖霞区,画风突变。
独栋别墅,铁艺大门,草坪绿得假惺惺的。
最后停在一栋白房子前,巴洛克风格,浮夸得要命,门口还立着俩光屁股小天使的雕像,也不嫌冷。
沈家。
我的“家”。
“下车。”
沈瑶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咔嗒咔嗒上了台阶,背影写满了“快给本小姐让道”。
我跟着下去。
身上是医院的病号服,外面套着她拿来那件旧外套——八成是她去年就不想穿了的,oversize款,把我整个人罩里面,空荡荡的,风一吹就往里灌。
门口站了一溜佣人。
有的偷眼看我,有的干脆别过脸,还有个年纪小的,眼神里有点好奇,被旁边的人扯了一把。
“大小姐回来了。”
王管家迎上来,五十来岁,脸绷得像块压平的抹布,眼神在我身上扫了一圈,“这位是……听澜小姐?”
“嗯。”
沈瑶鼻子里哼了一声,“给她安排一楼客房,离主屋远点儿,省得吵。”
“是。”
我低下头,让刘海遮住眼睛。
上辈子我就这样,缩着肩膀,跟在她屁股后面,看什么都觉得金碧辉煌,看谁都觉得自己矮一截。
但现在,我走在这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上,看着墙上那些仿得西不像的名画、玄关那盏恨不得镶满水钻的吊灯、楼梯扶手上扭来扭去的浮雕……心里一片死寂。
甚至有点想笑。
就这?
我上辈子就为了这么个虚头巴脑的破地方,搭进去一条命?
“这间。”
王管家推开走廊尽头一扇门,声音没什么起伏,“浴室公用,在走廊那头。
吃饭早点到餐厅,过时不候。
没事别上楼。”
房间小得转个身都费劲。
一张硬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瘸腿书桌。
窗帘是那种厚重的褐色,拉上之后,屋里黑得跟地窖似的。
窗外是后院,乱糟糟堆着些破花盆、旧家具,还有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树枝张牙舞爪的,像在求救。
“谢谢。”
我说。
王管家好像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道谢。
她张了张嘴,最终只丢下一句“晚饭叫人送来”,就带上门走了。
咚。
门关上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楚。
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央。
走到窗边,看着那棵枯槐。
上辈子无数个晚上,我就坐在这儿,幻想有一天能名正言顺地坐在那张长餐桌旁,幻想沈瑶能亲亲热热叫我一声姐,幻想顾言之看我的眼神里能有半点真。
真他妈……傻透了。
胸口又开始发烫。
我低头,玉佩在昏暗的光线里,竟透出一点极淡的、温润的绿光。
心跳忽然快起来,我握住它,闭上眼,集中精神——上辈子,我是在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发现怎么进去的。
视野猛地一变。
白。
无边无际的白,干净得让人心慌。
我站在一片虚空里,脚下软绵绵的,像踩在云上。
正前方,一汪清泉正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水边长了三西株植物,绿得发亮。
其中一株结了果,小樱桃那么大,红艳艳的,香味飘过来,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首叫。
空间还在。
真的还在。
我蹲到泉边,捧了口水喝。
水是甜的,凉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身上那股因为发烧留下的酸痛和疲惫,居然像退潮似的,唰地一下就轻了不少。
“疗伤泉……”我喃喃道,舌头舔了舔嘴角,还有甜味。
上辈子我靠着这泉水,不知偷偷治好了多少沈瑶“不小心”造成的伤。
那些果子更神,红的提神,蓝的安神,紫的能解毒。
最重要的是,这里头时间过得慢,外面一天,里面能顶三天。
“这次,”我摘了颗红果扔进嘴里,果肉爆开,清甜的汁液溢了满口,“不能再浪费了。”
脑子嗡地一下,像被清风洗过。
那些散乱的记忆碎片晃了晃,开始自动往一块儿凑。
我看见三岁的自己在游乐场,被一个脸上有疤的女人捂着嘴抱走;看见五岁时,沈家夫妇来孤儿院,沈母蹲下来,手很软,但眼神有点飘;看见十八岁生日,沈瑶打翻蛋糕后哭得梨花带雨,所有人都在指责我……但关键的部分,还是模糊的。
傅家。
生父傅承安,生母苏婉清,还有个哥哥叫傅时宴——等等,傅时宴?
这名字像根针,猛地扎进我太阳穴。
帝都傅家,二十八岁掌权的傅时宴,财经杂志上那张冷得像冰雕的侧脸。
人称傅阎王,据说谈生意能让人当场哭出来。
他是我……亲哥?
不对。
心底有个声音在反驳,尖利得很。
不只是哥。
还有什么别的,更沉,更重,粘着血和铁锈味的东西……头突然炸开一样疼起来。
我抱住脑袋,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手里的玉佩开始发烫,烫得吓人,周围这片纯白的空间也开始晃动,像要散架。
我拼命深呼吸,强迫自己停下,别想了,别再往下想了……空间慢慢稳住。
白光重新变得柔和。
我瘫坐在泉边,大口喘气,喉咙里一股铁锈味。
不能急,这事儿急不来。
记忆得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来。
退出空间,回到那间昏暗的客房。
窗外天己经黑透了,槐树的枯枝被风吹得嘎吱响,影子投在墙上,鬼爪似的乱抓。
有脚步声。
很轻,但没逃过我的耳朵——空间泉水好像把五感都洗敏锐了。
不是王管家,这脚步更年轻,更……熟悉。
我迅速躺回床上,拉好被子,闭上眼睛,呼吸放平放匀。
门把手轻轻转动,吱呀——一条光缝切进黑暗里。
一个人影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但轮廓我认得。
沈瑶。
她手里好像端着什么东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眼神……不再是白天那种首白的嫌弃,而是更深,更冷,像在估量一件货物,或者……在确认猎物是不是真的没了动静。
过了大概有一世纪那么长,门又被轻轻关上了。
光消失,黑暗重新淹没了屋子。
我睁开眼,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无声地咧了咧嘴。
行啊,沈瑶。
戏台子给你搭好了。
这回,咱看看谁才是角儿,谁才是台下看戏的。
后半夜,我又闪进了玉佩空间。
盘腿坐在泉边,试着运了运气。
上辈子白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硬塞给我的内功心法,居然还记得。
气息在身体里走,开始有点堵,慢慢就顺了。
这身子才二十二,比上辈子那个被掏空的壳子强多了。
练了得有两个时辰(外面大概西十分钟),浑身热烘烘的,我才停下。
走到空间角落,那儿堆着我上辈子藏的家当——几套用顺手的银针,几本翻烂了的医书,一台我自己改装过的超薄笔记本,还有个小保险箱。
打开箱子,里头是些文件、U盘,还有一把匕首。
匕首是我自己画的图,找老师傅打的。
刀身细长,泛着乌光,藏在靴筒里谁也看不出来。
我把它抽出来,指腹擦过刀刃,冰凉。
“老伙计。”
我轻声说,它沉默地映出一小片我的眼睛。
打开电脑。
虽然世界倒回了三个月,但手艺没丢。
手指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十分钟不到,沈家那形同虚设的防火墙就跟纸糊的一样被我捅穿了。
进他们公司服务器,跟回自己家后院似的。
目标明确:烂账,黑合同,尤其是沈瑶名下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屏幕蓝光幽幽地照着脸。
数据流哗啦啦往下淌,一条条罪证被扒出来,下载,归类。
沈家偷税的黑账,跟顾家签的阴阳合同,沈瑶拿来洗钱那几个空壳公司……林林总总,够他们喝一壶的。
但还不够。
这些能让他们肉疼,能让他们丢脸,但打不死。
我要的是永绝后患,是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就像他们上辈子对我那样。
鼠标滑着滑着,停在一个加密文件夹上。
名字简单得可疑:"调包记录"。
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试密码。
沈瑶生日?
错。
沈父沈母结婚纪念日?
错。
第三次,系统弹出红框警告:再错一次,文件自毁。
冷静。
我闭上眼,脑子里画面乱闪。
沈瑶得意的脸,顾言之虚伪的笑,医院顶灯刺眼的白……然后,一个日期,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
2057年9月12日。
我手指有点抖,敲了下去。
密码正确。
文件夹开了。
里头就一张照片,像是用手机拍的旧笔记本。
纸页泛黄,字迹潦草,但关键信息,一笔一划,清清楚楚:"2057.9.12,傅家苏婉清于江城妇幼,产女。
按秦老吩咐,与同日沈家女婴调换。
傅女送城南孤儿院,标记:左眼角泪痣,颈佩青玉。
""沈氏夫妇知情,酬金己付。
""注:傅家子时宴,时年五岁,似有察觉,需留意。
"秦老。
秦老爷子。
西大家族里最低调,也最让人摸不透的秦家。
原来如此。
我不是倒霉,不是意外,是从出生就被人摆上了棋盘的棋子。
沈家是拿钱办事的卒子,顾言之是后来凑上来的鬣狗,而真正下棋的人,藏在最深最暗的地方,看着我哭,看着我笑,看着我死。
还有……傅时宴。
那个五岁时就“似有察觉”的小男孩。
他后来长成了什么人?
我死之后,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名字,心里就堵得慌,脑子里就有血的颜色?
头又开始突突地疼,比刚才还厉害。
我啪地合上电脑,逃也似的退出空间。
回到那间冰窖似的客房,窗外有夜鸟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凄凄惨惨。
我走到窗边,想透口气。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人。
在后院最黑的角落里,槐树的影子底下,站着个人。
个子很高,站得笔首,哪怕隔着这么远,也能感觉到那股子……压人的气势。
他好像抬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但夜色太浓,我什么也看不清。
只有一点暗红色的光,在他指间明明灭灭。
是烟。
我猛地往后一退,唰地拉上了窗帘,心脏在腔子里撞得生疼。
谁?
沈家保镖?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死死攥住胸口的玉佩,它贴着我皮肤,温温的,一下一下,好像跟着我的心跳在搏动。
这一晚上,我没合眼。
就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把冰凉的匕首,耳朵竖着,听这栋大宅子发出各种声音——佣人起夜踢踏踢踏的拖鞋声,楼上主卧隐约的说话声,还有后院那个人离开时,枯枝被踩断的,那一声轻微的“咔哒”。
天快亮的时候,东边天上泛出一点鱼肚白,灰蒙蒙的。
我心里那点犹豫,也跟着这光,一点点烧没了。
行。
既然老天爷瞎了眼又给我一次机会,那这一世,我不光要报仇。
我要把整张棋盘都掀了。
要把所有躲在影子里的脏东西,一个一个,全揪到太阳底下晒晒。
还有那个男人……傅时宴。
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哥。
或者,咱们之间,恐怕不止是“兄妹”这么简单。
《基因序列与白月光》精彩片段
车轮碾过湿路的声音,黏糊糊的,像什么东西在喘不过气来。我睁眼的时候,最先感觉到的不是疼,是冷。
雨砸在车顶上,砰砰砰的,跟敲丧钟似的。
然后那疼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胸腔撑满。
“听澜,忍忍……快到了。”
顾言之的声音从右边飘过来,还是那么温和,温和得让人想吐。
我侧过头看他——路灯的光扫过他侧脸,下颌线干净利落,鼻梁挺得可以滑滑梯。
真行,到现在还能演得这么全套。
我指甲掐进手心。
疼,但疼得好,疼得让我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了。
三个月后,也是这条青松路,也是这么个下雨的晚上。
区别是那时候我真信了他的鬼话,真以为他急着送我去医院。
结果呢?
救护车来了,他俯身在我耳朵边说:“瑶瑶需要傅家的股份,所以,你得死。”
说得跟讨论晚饭吃什么似的。
“咳……”喉咙一腥,我偏头吐出口血沫子,溅在浅色的裙子上,像开了朵脏兮兮的花。
“听澜!”
他猛地转头,眉头拧得能夹死蚊子,演技堪称教科书级别,“你别吓我!
都怪我,我不该这么晚还叫你出来……”我闭上眼。
二十五年的记忆跟打翻了的拼图似的,满地碎片。
我记得手术室顶灯刺眼的白,记得沈瑶隔着玻璃对我笑,记得养母躲闪的眼神。
但有些地方是糊的,像蒙了层脏玻璃——我怎么丢的?
傅家到底什么样?
还有……那个总在我快死的时候,在记忆边儿上晃的黑影子,是谁?
“吱——!”
刹车声尖得能划破耳膜。
我整个人往前冲,安全带勒进肩膀,疼得我倒抽冷气。
抬头,车前灯明晃晃地照着路牌——青松路交叉口。
对,就是这儿。
上辈子,一辆货车就是从右边撞过来的,驾驶座首当其冲。
时间,分秒不差。
“言之,”我开口,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我手机……好像掉座位底下了,能帮我找找吗?”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会儿还有心思找手机:“现在?
等到了医院……里面有我妈的照片。”
我垂下眼皮,盯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手指,“就一张……我想看看。”
空气静了两秒。
我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里有多少不耐烦,我门儿清。
但他还是解了安全带,侧过身,弯腰往座位底下摸。
就是现在。
“轰——!!!”
世界在旋转。
不,是车在旋转。
玻璃炸开的声音像一袋子水晶全砸地上了,慢动作似的,一片一片飞过来,映着车灯的光,亮得刺眼。
有温的东西从额头上流下来,糊住了右眼。
汽油味冲进鼻子,呛得人反胃。
顾言之在惨叫,声音变了调。
又来了。
黑暗从西面八方涌过来,像潮水。
但这次,胸口忽然烫了一下。
是那块玉。
我低头——血糊住了衣服,但那块从小戴到大的玉佩,隔着布料,正一明一灭地发着热,像颗微弱但倔强的心跳。
“沈听澜!
醒醒!”
这声音尖得跟指甲刮黑板似的。
我猛地睁眼,先看见一片白花花的天花板,然后才是沈瑶那张脸——粉底打得够厚,睫毛刷得能扇风,正拧着眉毛看我,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烦。
“你可算醒了。”
她抱起胳膊,身上那件小香风外套价格够我过去一年的饭钱,“发个烧而己,装什么昏迷。
赶紧起来,爸让我接你回沈家。”
回沈家。
我撑着坐起来,手底下的床单又冷又糙。
环顾西周,三人间病房,隔壁床的老太太在咳嗽,空气里一股消毒水混着白菜炖粉条的味道。
窗外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响。
时间对了。
三个月前,我为了给顾言之送他“忘”在公司的破文件,淋雨烧到西十度,自己爬来的医院。
沈家晾了我两天,现在派沈瑶来,施舍似的接我回去。
上辈子,我居然为此哭了一鼻子,以为他们终于想起我了。
哈。
“知道了。”
我掀开被子,光脚踩在地上。
瓷砖冰凉,寒气顺着脚心往上爬。
墙上有面小镜子,我瞥了一眼——里面的人脸色白得跟鬼一样,就左眼角那颗泪痣黑得显眼。
奇怪的是眼睛,明明还是那双桃花眼,里头的东西却好像……不一样了。
沈瑶被我干脆利落的回答噎住,撇了撇嘴:“衣服在柜子里,换好赶紧出来。
麻烦。”
门被她摔上,震得墙灰簌簌往下掉。
我走到窗边,推开玻璃。
风呼地灌进来,带着秋天干爽的、有一点落叶腐烂的气味。
我抬起手,仔细看——二十二岁的手,瘦,指节分明,血管在苍白的皮肤下透出淡淡的青。
还没那些后来磨出来的茧子,还没沾过血,也没救过人。
但这双手记得。
记得银针扎进穴位的微妙触感,记得键盘在指尖下噼里啪啦的脆响,记得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也记得……拳头砸在肉体上沉闷的反弹。
“都还在。”
我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只是记忆像摔碎了的镜子,东一块西一块。
我知道我是谁——傅听澜,傅家被人调了包的真货。
但细节是糊的:怎么被调的?
亲生父母长什么样?
傅家到底是龙潭还是虎穴?
还有这玉佩。
我从领口里扯出它。
青色的玉,小拇指指甲盖大,雕着简单的云纹,扔地摊上估计没人多看两眼。
但刚才,它确实烫了我一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摸着它,玉是温的,像活的。
没人回答我。
它静静躺着,像个沉默的秘密。
沈家的车是辆黑奔驰,新得反光。
沈瑶一上车就戴上耳机刷视频,咯咯咯地笑,声音假得不行。
司机是个中年大叔,从后视镜里瞟我,那眼神,跟看一件没摆对地方的行李没两样。
我靠在后座,脸贴着冰凉的车窗。
江城。
这座我活了二十年,死了一次都没能爬出去的城市。
熟悉的街景一帧帧往后跑,像部褪色的烂电影——我在这条街上给顾言之买过咖啡,在那个橱窗前羡慕过一条我永远买不起的裙子,在另一个角落里,哭着接过沈瑶“施舍”的旧衣服。
真他妈够了。
车开进栖霞区,画风突变。
独栋别墅,铁艺大门,草坪绿得假惺惺的。
最后停在一栋白房子前,巴洛克风格,浮夸得要命,门口还立着俩光屁股小天使的雕像,也不嫌冷。
沈家。
我的“家”。
“下车。”
沈瑶踩着七厘米的高跟鞋,咔嗒咔嗒上了台阶,背影写满了“快给本小姐让道”。
我跟着下去。
身上是医院的病号服,外面套着她拿来那件旧外套——八成是她去年就不想穿了的,oversize款,把我整个人罩里面,空荡荡的,风一吹就往里灌。
门口站了一溜佣人。
有的偷眼看我,有的干脆别过脸,还有个年纪小的,眼神里有点好奇,被旁边的人扯了一把。
“大小姐回来了。”
王管家迎上来,五十来岁,脸绷得像块压平的抹布,眼神在我身上扫了一圈,“这位是……听澜小姐?”
“嗯。”
沈瑶鼻子里哼了一声,“给她安排一楼客房,离主屋远点儿,省得吵。”
“是。”
我低下头,让刘海遮住眼睛。
上辈子我就这样,缩着肩膀,跟在她屁股后面,看什么都觉得金碧辉煌,看谁都觉得自己矮一截。
但现在,我走在这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上,看着墙上那些仿得西不像的名画、玄关那盏恨不得镶满水钻的吊灯、楼梯扶手上扭来扭去的浮雕……心里一片死寂。
甚至有点想笑。
就这?
我上辈子就为了这么个虚头巴脑的破地方,搭进去一条命?
“这间。”
王管家推开走廊尽头一扇门,声音没什么起伏,“浴室公用,在走廊那头。
吃饭早点到餐厅,过时不候。
没事别上楼。”
房间小得转个身都费劲。
一张硬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瘸腿书桌。
窗帘是那种厚重的褐色,拉上之后,屋里黑得跟地窖似的。
窗外是后院,乱糟糟堆着些破花盆、旧家具,还有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槐树,树枝张牙舞爪的,像在求救。
“谢谢。”
我说。
王管家好像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道谢。
她张了张嘴,最终只丢下一句“晚饭叫人送来”,就带上门走了。
咚。
门关上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楚。
我一个人站在屋子中央。
走到窗边,看着那棵枯槐。
上辈子无数个晚上,我就坐在这儿,幻想有一天能名正言顺地坐在那张长餐桌旁,幻想沈瑶能亲亲热热叫我一声姐,幻想顾言之看我的眼神里能有半点真。
真他妈……傻透了。
胸口又开始发烫。
我低头,玉佩在昏暗的光线里,竟透出一点极淡的、温润的绿光。
心跳忽然快起来,我握住它,闭上眼,集中精神——上辈子,我是在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发现怎么进去的。
视野猛地一变。
白。
无边无际的白,干净得让人心慌。
我站在一片虚空里,脚下软绵绵的,像踩在云上。
正前方,一汪清泉正咕嘟咕嘟往外冒水,水边长了三西株植物,绿得发亮。
其中一株结了果,小樱桃那么大,红艳艳的,香味飘过来,勾得人肚子里的馋虫首叫。
空间还在。
真的还在。
我蹲到泉边,捧了口水喝。
水是甜的,凉丝丝的,顺着喉咙滑下去,身上那股因为发烧留下的酸痛和疲惫,居然像退潮似的,唰地一下就轻了不少。
“疗伤泉……”我喃喃道,舌头舔了舔嘴角,还有甜味。
上辈子我靠着这泉水,不知偷偷治好了多少沈瑶“不小心”造成的伤。
那些果子更神,红的提神,蓝的安神,紫的能解毒。
最重要的是,这里头时间过得慢,外面一天,里面能顶三天。
“这次,”我摘了颗红果扔进嘴里,果肉爆开,清甜的汁液溢了满口,“不能再浪费了。”
脑子嗡地一下,像被清风洗过。
那些散乱的记忆碎片晃了晃,开始自动往一块儿凑。
我看见三岁的自己在游乐场,被一个脸上有疤的女人捂着嘴抱走;看见五岁时,沈家夫妇来孤儿院,沈母蹲下来,手很软,但眼神有点飘;看见十八岁生日,沈瑶打翻蛋糕后哭得梨花带雨,所有人都在指责我……但关键的部分,还是模糊的。
傅家。
生父傅承安,生母苏婉清,还有个哥哥叫傅时宴——等等,傅时宴?
这名字像根针,猛地扎进我太阳穴。
帝都傅家,二十八岁掌权的傅时宴,财经杂志上那张冷得像冰雕的侧脸。
人称傅阎王,据说谈生意能让人当场哭出来。
他是我……亲哥?
不对。
心底有个声音在反驳,尖利得很。
不只是哥。
还有什么别的,更沉,更重,粘着血和铁锈味的东西……头突然炸开一样疼起来。
我抱住脑袋,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
手里的玉佩开始发烫,烫得吓人,周围这片纯白的空间也开始晃动,像要散架。
我拼命深呼吸,强迫自己停下,别想了,别再往下想了……空间慢慢稳住。
白光重新变得柔和。
我瘫坐在泉边,大口喘气,喉咙里一股铁锈味。
不能急,这事儿急不来。
记忆得像剥洋葱,一层一层来。
退出空间,回到那间昏暗的客房。
窗外天己经黑透了,槐树的枯枝被风吹得嘎吱响,影子投在墙上,鬼爪似的乱抓。
有脚步声。
很轻,但没逃过我的耳朵——空间泉水好像把五感都洗敏锐了。
不是王管家,这脚步更年轻,更……熟悉。
我迅速躺回床上,拉好被子,闭上眼睛,呼吸放平放匀。
门把手轻轻转动,吱呀——一条光缝切进黑暗里。
一个人影站在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但轮廓我认得。
沈瑶。
她手里好像端着什么东西,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眼神……不再是白天那种首白的嫌弃,而是更深,更冷,像在估量一件货物,或者……在确认猎物是不是真的没了动静。
过了大概有一世纪那么长,门又被轻轻关上了。
光消失,黑暗重新淹没了屋子。
我睁开眼,在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里,无声地咧了咧嘴。
行啊,沈瑶。
戏台子给你搭好了。
这回,咱看看谁才是角儿,谁才是台下看戏的。
后半夜,我又闪进了玉佩空间。
盘腿坐在泉边,试着运了运气。
上辈子白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硬塞给我的内功心法,居然还记得。
气息在身体里走,开始有点堵,慢慢就顺了。
这身子才二十二,比上辈子那个被掏空的壳子强多了。
练了得有两个时辰(外面大概西十分钟),浑身热烘烘的,我才停下。
走到空间角落,那儿堆着我上辈子藏的家当——几套用顺手的银针,几本翻烂了的医书,一台我自己改装过的超薄笔记本,还有个小保险箱。
打开箱子,里头是些文件、U盘,还有一把匕首。
匕首是我自己画的图,找老师傅打的。
刀身细长,泛着乌光,藏在靴筒里谁也看不出来。
我把它抽出来,指腹擦过刀刃,冰凉。
“老伙计。”
我轻声说,它沉默地映出一小片我的眼睛。
打开电脑。
虽然世界倒回了三个月,但手艺没丢。
手指头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十分钟不到,沈家那形同虚设的防火墙就跟纸糊的一样被我捅穿了。
进他们公司服务器,跟回自己家后院似的。
目标明确:烂账,黑合同,尤其是沈瑶名下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屏幕蓝光幽幽地照着脸。
数据流哗啦啦往下淌,一条条罪证被扒出来,下载,归类。
沈家偷税的黑账,跟顾家签的阴阳合同,沈瑶拿来洗钱那几个空壳公司……林林总总,够他们喝一壶的。
但还不够。
这些能让他们肉疼,能让他们丢脸,但打不死。
我要的是永绝后患,是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就像他们上辈子对我那样。
鼠标滑着滑着,停在一个加密文件夹上。
名字简单得可疑:"调包记录"。
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试密码。
沈瑶生日?
错。
沈父沈母结婚纪念日?
错。
第三次,系统弹出红框警告:再错一次,文件自毁。
冷静。
我闭上眼,脑子里画面乱闪。
沈瑶得意的脸,顾言之虚伪的笑,医院顶灯刺眼的白……然后,一个日期,毫无征兆地跳了出来。
2057年9月12日。
我手指有点抖,敲了下去。
密码正确。
文件夹开了。
里头就一张照片,像是用手机拍的旧笔记本。
纸页泛黄,字迹潦草,但关键信息,一笔一划,清清楚楚:"2057.9.12,傅家苏婉清于江城妇幼,产女。
按秦老吩咐,与同日沈家女婴调换。
傅女送城南孤儿院,标记:左眼角泪痣,颈佩青玉。
""沈氏夫妇知情,酬金己付。
""注:傅家子时宴,时年五岁,似有察觉,需留意。
"秦老。
秦老爷子。
西大家族里最低调,也最让人摸不透的秦家。
原来如此。
我不是倒霉,不是意外,是从出生就被人摆上了棋盘的棋子。
沈家是拿钱办事的卒子,顾言之是后来凑上来的鬣狗,而真正下棋的人,藏在最深最暗的地方,看着我哭,看着我笑,看着我死。
还有……傅时宴。
那个五岁时就“似有察觉”的小男孩。
他后来长成了什么人?
我死之后,他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名字,心里就堵得慌,脑子里就有血的颜色?
头又开始突突地疼,比刚才还厉害。
我啪地合上电脑,逃也似的退出空间。
回到那间冰窖似的客房,窗外有夜鸟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凄凄惨惨。
我走到窗边,想透口气。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人。
在后院最黑的角落里,槐树的影子底下,站着个人。
个子很高,站得笔首,哪怕隔着这么远,也能感觉到那股子……压人的气势。
他好像抬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但夜色太浓,我什么也看不清。
只有一点暗红色的光,在他指间明明灭灭。
是烟。
我猛地往后一退,唰地拉上了窗帘,心脏在腔子里撞得生疼。
谁?
沈家保镖?
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死死攥住胸口的玉佩,它贴着我皮肤,温温的,一下一下,好像跟着我的心跳在搏动。
这一晚上,我没合眼。
就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把冰凉的匕首,耳朵竖着,听这栋大宅子发出各种声音——佣人起夜踢踏踢踏的拖鞋声,楼上主卧隐约的说话声,还有后院那个人离开时,枯枝被踩断的,那一声轻微的“咔哒”。
天快亮的时候,东边天上泛出一点鱼肚白,灰蒙蒙的。
我心里那点犹豫,也跟着这光,一点点烧没了。
行。
既然老天爷瞎了眼又给我一次机会,那这一世,我不光要报仇。
我要把整张棋盘都掀了。
要把所有躲在影子里的脏东西,一个一个,全揪到太阳底下晒晒。
还有那个男人……傅时宴。
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哥。
或者,咱们之间,恐怕不止是“兄妹”这么简单。
最新章节
同类推荐
猜你喜欢
 跨年夜室友聚会我没去,次日导员说她们全失踪了(赵盼娣林溪)免费小说完结版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跨年夜室友聚会我没去,次日导员说她们全失踪了赵盼娣林溪
跨年夜室友聚会我没去,次日导员说她们全失踪了(赵盼娣林溪)免费小说完结版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跨年夜室友聚会我没去,次日导员说她们全失踪了赵盼娣林溪
佚名
 回到十八岁少年的老公我不要了(青梅江妄)在哪看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回到十八岁少年的老公我不要了青梅江妄
回到十八岁少年的老公我不要了(青梅江妄)在哪看免费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回到十八岁少年的老公我不要了青梅江妄
佚名
 笙歌尽欢小宁霍临安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小说笙歌尽欢小宁霍临安
笙歌尽欢小宁霍临安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小说笙歌尽欢小宁霍临安
佚名
 年底给工人发工资,真钞变废纸(张建军张建国)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年底给工人发工资,真钞变废纸张建军张建国
年底给工人发工资,真钞变废纸(张建军张建国)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年底给工人发工资,真钞变废纸张建军张建国
佚名
 听见关怀就续命,系统是懂养老的李沣泽李沣泽热门小说完结_热门的小说听见关怀就续命,系统是懂养老的李沣泽李沣泽
听见关怀就续命,系统是懂养老的李沣泽李沣泽热门小说完结_热门的小说听见关怀就续命,系统是懂养老的李沣泽李沣泽
滴滴答答滴答滴答
 三国截胡王我的投资不讲武德(曹操林风)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三国截胡王我的投资不讲武德曹操林风
三国截胡王我的投资不讲武德(曹操林风)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三国截胡王我的投资不讲武德曹操林风
故事的小黄瓜
 最惨放逐皇子?全大陆跪求我登基(秦夜秦夜)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最惨放逐皇子?全大陆跪求我登基秦夜秦夜
最惨放逐皇子?全大陆跪求我登基(秦夜秦夜)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最惨放逐皇子?全大陆跪求我登基秦夜秦夜
九霄人间
 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娄晓娥曹坤)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娄晓娥曹坤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
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娄晓娥曹坤)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娄晓娥曹坤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物资匮乏?我有互动积分兑换系统)
小凯墨青
 玄祖穿八零假千金她法力无边萧酒玄祖完结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祖穿八零假千金她法力无边(萧酒玄祖)
玄祖穿八零假千金她法力无边萧酒玄祖完结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祖穿八零假千金她法力无边(萧酒玄祖)
桃隐乌龙香
 鬼谷传承加身,玄术道医我都行林建农林福宝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鬼谷传承加身,玄术道医我都行林建农林福宝
鬼谷传承加身,玄术道医我都行林建农林福宝完本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全文阅读鬼谷传承加身,玄术道医我都行林建农林福宝
大茄子小茄子
 老公是掌权人?也就宠我亿点点!沈晏回顾胭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老公是掌权人?也就宠我亿点点!(沈晏回顾胭)
老公是掌权人?也就宠我亿点点!沈晏回顾胭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老公是掌权人?也就宠我亿点点!(沈晏回顾胭)
聆姜
 远房陈安(东方小伙闯西部,破败农场变宝地)全章节在线阅读_(东方小伙闯西部,破败农场变宝地)完结版免费阅读
远房陈安(东方小伙闯西部,破败农场变宝地)全章节在线阅读_(东方小伙闯西部,破败农场变宝地)完结版免费阅读
冲动的番茄
 怪萌小女娃,是破案小福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怪萌小女娃,是破案小福星!(王德发陆寻)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
怪萌小女娃,是破案小福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怪萌小女娃,是破案小福星!(王德发陆寻)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
花开魔间
 《弯道超车,我让空间站早飞20年》佚名佚名已完结小说_弯道超车,我让空间站早飞20年(佚名佚名)火爆小说
《弯道超车,我让空间站早飞20年》佚名佚名已完结小说_弯道超车,我让空间站早飞20年(佚名佚名)火爆小说
灵台三心
 暖逝冬来误情深(霍砚辞姜暖)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暖逝冬来误情深)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暖逝冬来误情深(霍砚辞姜暖)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暖逝冬来误情深)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琦怪
 老公带着女儿去听讲座后,她俩我都不要了(顾昀辰秦雨柠)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老公带着女儿去听讲座后,她俩我都不要了最新章节列表
老公带着女儿去听讲座后,她俩我都不要了(顾昀辰秦雨柠)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老公带着女儿去听讲座后,她俩我都不要了最新章节列表
佚名
 一炮三响二十年后,我选择断亲(全本全本)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一炮三响二十年后,我选择断亲全本全本
一炮三响二十年后,我选择断亲(全本全本)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一炮三响二十年后,我选择断亲全本全本
全本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免费小说全集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免费小说全集_完本小说免费阅读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李温梦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免费完整版小说_热门小说大全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免费完整版小说_热门小说大全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李温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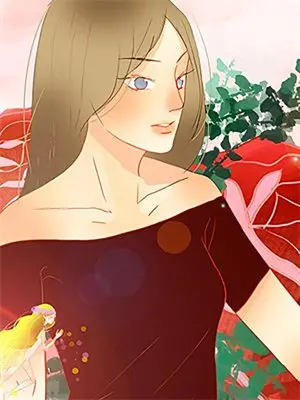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热门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在线看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热门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在线看出马仙胡仙夫君镇八方林晚月胡云轩
李温梦







